北京 楊敏如
临湖轩以东的未名湖一片碧波清水,那湖光塔影,那岛亭柳岸,可称燕园胜景之最。第一次瞥见它,它便使我感受到只有在母亲怀中才有的温暖和安谧…
秋深了。独自黄昏,多番陷入回忆与遐想中。往往在这时,心底荡漾起那深深爱恋着的未名湖水的涟漪。它依傍着衰柳、白云、石舫、水塔,亲切地聆听着我这七十年前的老友的倾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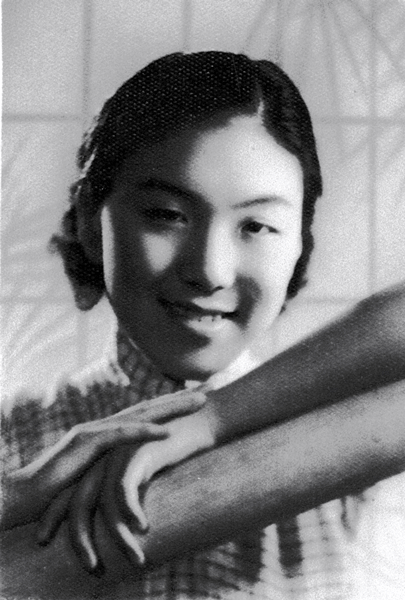 1934 年,我十八岁,来到多处呈现大自然之美和古老文化气息的北京,进入私立燕京大学读中文系。第一使我惊喜莫名的是这今古交融、中西合璧的校园。那堂皇宫殿似 的建筑:一对石狮守护着厚重大门,迎面是蓝空下的白玉华表。巍峨鼎立的是贝公、穆、睿三座教学楼。向右深入,则见庄严的图书馆,玲珑的姊妹楼。在佳木葱 茏、芳草如茵中,较远卓然独立的是适楼,较高龟驮石碑处有钟亭,旁侧有大体育馆和琴室,呵护着作为女生宿舍的两两相对的四个院落。各院门首覆着紫色的藤 萝,墙上铺有秋冬的红叶,门外边有迎春、桃花、李花、丁香花衬托着女生们的贵重气质。这可是深闺。男生们一年才准进来窥探一次。但这一切都比不上潇洒的临 湖轩以东的未名湖一片碧波清水,那湖光塔影,那岛亭柳岸,可称燕园胜景之最。第一次瞥见它,它便使我感受到只有在母亲怀中才有的温暖和安谧,我向它注目, 它绽开笑容,似乎说:“新同学,欢迎你,这里将是你四年的新家!”
1934 年,我十八岁,来到多处呈现大自然之美和古老文化气息的北京,进入私立燕京大学读中文系。第一使我惊喜莫名的是这今古交融、中西合璧的校园。那堂皇宫殿似 的建筑:一对石狮守护着厚重大门,迎面是蓝空下的白玉华表。巍峨鼎立的是贝公、穆、睿三座教学楼。向右深入,则见庄严的图书馆,玲珑的姊妹楼。在佳木葱 茏、芳草如茵中,较远卓然独立的是适楼,较高龟驮石碑处有钟亭,旁侧有大体育馆和琴室,呵护着作为女生宿舍的两两相对的四个院落。各院门首覆着紫色的藤 萝,墙上铺有秋冬的红叶,门外边有迎春、桃花、李花、丁香花衬托着女生们的贵重气质。这可是深闺。男生们一年才准进来窥探一次。但这一切都比不上潇洒的临 湖轩以东的未名湖一片碧波清水,那湖光塔影,那岛亭柳岸,可称燕园胜景之最。第一次瞥见它,它便使我感受到只有在母亲怀中才有的温暖和安谧,我向它注目, 它绽开笑容,似乎说:“新同学,欢迎你,这里将是你四年的新家!”
才住下来,就收到女部的邀请,要我们穿上出门作客的衣服,在一所华丽的厅堂里,会见部分教师和同年级的各系女生。第一位笑盈盈迎接我们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雷洁琼(这里我 恭敬地祝贺她百岁寿诞!)她用广东腔的普通话向我们作自我介绍:“我是雷洁琼,我是你们的导师(音如“肚丝”!)。”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风格和模样的同级各 系同学,也一一握手相认。还有一些被请的男女教师,也作了简短的欢迎辞,并且不无幽默地夸耀所主的各系和其特点。我感到自己被尊重为大人,不像在家或在中 学里,只会被母亲和老师当作孩子、后辈,再三地叫我听话,一味地叫我用功。
以后是选课,先到贝公楼系里见到中文系主任,背后大墙 上张贴着课程名称与学分及任课老师姓名,可参照文科、理科、主修、副修的分界与要求,自己把要选的课记下来。有的课是外系的,需要到别的楼去登记姓名。最 后手续是请系主任签名认可。只见到处是骑自行车或步行的学生,兴高采烈,蜜蜂一样地穿梭出进采集、寻觅,或抢先在叫座的名课单上签名(超出限定人数,就只 能做旁听生了)。我那时也严肃起来,仿佛不是为母亲、为虚名、为糊口而读书,恐怕真是为珍贵的一生负责了。那一年级的课程——教授的阵容与课程的深奥就令 我咋舌:1、大一国文一班,任课教师是中文系主任郭绍虞教授;2、大一英文A班,任课教师是外语系主任谢迪克教授(H.Shadick);3、普通生物 学,任课教师是生物系主任李汝祺教授;4、普通心理学,任课教师是校长兼心理系主任陆志韦教授。由此可见学校对一年级学生的重视与培养。每课配备助教,课 堂的与实验室的。学生从课堂的教学深深觉出教授的渊博与诚恳,再于辅助教学的图书馆中得到更宽厚的知识,才真正知道求知的乐趣。我在中学,成绩平平;来到 燕京,成绩出现了飞跃。同来的同学笑着说:“杨敏如念书开窍了!”
当然图书馆是我没有一天(除星期日外)不到的地方。图书馆的特 点是肃静,你可以听到足声,衣裳窸窣声,椅子挪动声,从地下室提上书来的辘轳声,但是你难得听见人的笑语声。偶然有人交头接耳,只要旁边看书的人抬起头 来,对他一望,就立刻没有声息了。最快乐的是当读完留下的作业,伸伸腰,走到查书的柜子旁,找出一本自己想看的书,很快把它借到手,回到座位上恣情地看 着。有过一二次,竟忽略了时间,忘记了上课。
作中文系学生,似乎更加繁忙。每位教授轮流请我们做客,老师们讲着他们正在研究的题 目,或买到什么宝贝的书等,我们如坐春风,贪婪地聆听他们的高论,吸取他们的心得、观点。光是研究生就足以使我们一年级生惊佩不已。吴世昌高谈阔论,他在 批评胡适;陈梦家在讲文字、音韵,而我却只知他是新月派诗人;更有一次,主任把我们聚在未名湖的岛亭上,聆赏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谷音社来唱昆曲。清华大学中 文系俞平伯、朱自清、浦江清等名教授平时都还没见过。听他们唱,真是如听仙乐。郭绍虞见我喜爱昆曲,便常邀我去他家,他按风琴,我和师母、大妹唱着玩。曾 请到杨荫浏先生为我们拍《出塞》。有趣的是不用工尺谱,而用五线谱。后来在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中央大学词曲教授唐圭璋,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 生、谷音社台柱陶光都正在南中教课,我们纠集一些爱好昆曲的同事,每周末在我家学唱昆曲,时间一长,名扬于外,颇有一些名人闻声而至,如胡小石、卢冀野、 吴白匋、张充和、章元善等,无不引吭高歌。一声“漫拭英雄泪”(《山门》),正好宣泄一下对残暴的日军和乌烟瘴气的国民党政府的积愤。
我们中文系还有冰心师的义务授课《新文艺习作》。没有大纲,没有专论,她的课十分动听,记得她讲《西厢记》中两句:“猛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 长亭,减了玉肌。”经她一解,我越读越有味,渐渐迷上了中国艺术语言之美。这样的出自个人创作经验和感受的教课,我认为是金针度人的传授,怎不叫人感动! 以后几十年我也学会这种倾心而教的方法,也一样赢得学生的感佩。期末考试,更是妙绝,冰心师叫我们每人出一本杂志,一个人既是作者,也是主编、责编,乃至 封面、插图、美术、装订全都要自己来,我不仅因得了好分数而高兴,更令我高兴的这种考试方法真能使教师对学生的文化程度、作事能力、思想、心态都了解透彻 了。可惜我教了一辈子书,不能尝试这一好方法。当然冰心师不只一次带我们到未名湖上的石舫,她的性格就像那一泓秋水,睿智、温和、深情、循循善诱。我们女 生尤其喜欢听她现身说法地谈爱情和人生,有的女生愿意向她倾诉自己在爱情中的困惑、犹豫和痛苦,希望听到她的分析和忠告;解放后,我又从她学到了坚毅和勇 敢。她的丈夫和儿子被诬为右派,加上“文革”时面对的猛风暴雨,她都挺过来了。自吴老逝世,她又偏瘫,冰心师反而登上生命的最高峰,她从不能写字练到写就 一笔苍劲秀拔的好字,她每天写作不已,仍旧以天下为己任,以文笔作戈矛。她笑着对我说:“每天写几百字。登不出来就往抽屉一放,这叫‘抽屉文学’。”
同学中有不少人知道我对英文系主任谢迪克教授的“崇拜”。他确实是位挺负责任的好老师。那时我们的大一英文,用的是学校自选的英文名篇——诗歌和散文。他迈 着八字脚,操着英国音,在学生座位的行列中一边走着,一边吟哦着莎士比亚的诗。除读书外,每星期要交篇作文。把纸叠成两半,文写在右半张纸上,左半张纸留 给老师批改。隔一个月,学生拿着写过、改过的文稿,到办公室去见他,他再亲自对你指点。所以,一年下来,我把常犯的文法错误及用词不当都纠正过来,打好了 我的英文基础。他还请助教赵萝蕤大姐给我们上翻译课。记得有一次译的是鲁迅先生《药》中的一段,我听说当时谢教授对鲁迅的著作已有很深的造诣了。赵先生在 我的卷子上没有写“good”,而写了“好”,我觉得十分光彩。几十年后,山河依旧,人事沧桑,忽然听说谢教授重返燕园,他带来了对燕园的依恋和对中国的 友情。他身上携有两个名单:一个是他教过的学生的名字和成绩,另一个是他最希望见到的学生和朋友。他很高兴见到我,因为他从名单上查到我的姓名、班次和分 数——最高分“9”。他听说我的嫂嫂戴乃迭是从前他的同国籍同事戴乐仁(J.B.Taylon)的女儿后,想见我的哥哥杨宪益和嫂嫂,一叙友情。同时使他 伤心是的一些他想见的朋友,学生如顾随、吴世昌、子冈、吴兴华都先后离世了。他提出要为北大学生上课。当年美日宣战,日军闯入燕园时,他正为学生上《罗密 欧与朱丽叶》。此日重来,他要再讲莎翁此剧,圆上这个梦。连续讲了几日,我和赵萝蕤先生,每日清晨由城里赶到北大去听课,课室赶上修缮,很不洁净,学生不 惯听英语课,课堂秩序不好,虽有前排我们几个频频点头会意,我看他还是有点失望的。但是燕大的老同事、老同学热烈地欢迎他,请他吃饭,听昆曲,见过侯宝 林,在看到新中国的许多新气象后,他还是满意而归。听同学黄宗江说,他曾在美国谢师的家中做客,康奈尔大学环境优美,谢师用许多上品的西洋音乐待客,他的 书架上有顾师的书。原来我离开燕园后,谢师就去顾师班上旁听词曲了。我听了后,十分羡慕黄宗江,但是以后是不能再和谢迪克老师见面的了。
进入燕园,宛如进入一个团结友爱、良师益友的群体,每人不仅拥有同乡同系同中学同宿舍的朋友,还会有完全陌生的、不大理解的、不同气味的但终于熟悉了、理解 了、臭味相投了的好伙伴。在燕京,仿佛有什么魔法,把我们燕京人都融成一片。这里尊重独立、自由的思想,没有等级观念和精神压力。我得天独厚,来自教会学 校,二年级就加入了以宗教名义结成的团契——光盐团。“光盐”二字,来自圣经,意思是做人类的光和盐,正是人类所亟需的光亮和咸味。我和契友们,不分男 女、班次、系别,只要觉得“光盐”的要求符合自己的心愿,就可以成为兄弟姊妹,结为契友,我们这里有龚澎(原名维航),一二九后有了觉悟,参加了革命,在 外交工作上立了功,我们颇以她为荣。还有王锺翰、金奎与杨友凤,都是契友中的佼佼者,不幸曾被诬为右派,我们藏起同情,封闭了来往,直到噩梦过去,才敢格 外珍惜他们。现在,存留的契友仍旧坦诚相与,互助友爱,远在国外的常通款曲,如孙幼云、费美云等,同在北京的是亲密知己,如杨友凤、卢乐山等,几十年关爱和友情的给与,如今近九十岁,竟得到加倍的力量和安慰。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陷于敌手,我和一些住在天津租界的同学,没有听 到枪炮响,没有看见日本兵,就沦为亡国奴了。半年后,学校通知我们返校复课,系里也来信要我完成最后一年学业,我就于1938年春天回到燕大,读完课程。 一年后,又值春季,拿不到学士文凭,系主任叫我当系秘书,半年后,和35级一起毕业了。系主任叫我攻读研究生,我已无心读书,又磨蹭了半年,终于有机会去 重庆大后方。在燕京一共五年半,才结束了一生的读书生活。
1938年春天,我经过津京火车站和西直门两道屈辱性的盘查与搜身,来 到悬挂美国国旗的燕大,校园宛然,师生依旧,春天的桃花、李花开着,钟亭的钟声响着,但是,风雨如磐,山河破碎,未名湖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燕园失去了往日 的生气,一切都在黯淡中。“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真理在哪里?自由已失去!人民水深火热,空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首 先我将补足遗下的课。我从二年级上顾随先生的词曲课,学习填词,就得到顾师的赏识。但是我从来不敢登门造诣,甚至不敢到教员休息室单独求教。此刻,半年不 见,先生老了许多,他身体不好,坐骨神经痛,上课时穿着棉袍子,夹着椅垫子,进了课堂,放下书包,抬头用温和的目光扫视我们一遍,再从书包中拿出经他批改 的我们的上周作业,往桌的右角一放,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他昨夜不眠时作的词,开始娓娓地谈论起来。待读到一首宋词时,兴致全来了,目光炯炯,语句有声, 一片神行,旁征博引,把他的心、神、学问、灵魂全交给我们了。此时他的课更多的是弦外之音,常自称是弱者,以自嘲掩饰痛苦,其实在我们看来他才是真正的清 醒者和勇者。批改学生之词,更便于他激励同学。我曾写过这些词句:“相期相望,重山重水,渐行渐远。”他给我密密麻麻画了许多圈圈,却没有一句评语,但我 也能心领神会。当时,中文系请来周作人讲什么《颜氏家训》,学生对他的抵抗表现在不选他的课,这一招很灵,因为够不上八个人,他就不能上课,只好灰溜溜地 走了,本要增加日语课,请来周作人之子,此人在燕大十分孤独,人戏呼其绰号:“人头太次郎”。不少西籍教师主动保护学生,校车在西直门停下检查时,同学多 把自己携带的书包掷给西籍教师,他们无不帮助掩护。人传夏仁德先生最善于帮助进步同学脱离险境,送到后方。一天,他在宗教学院做礼拜讲演,题目是“耶稣的 不妥协精神”,大受欢迎。
拿到学士文凭,我的心更茫然了,我一直在设法寻求一条稳妥、安全到大后方的路,这时,系主任叫我考研究 生,读硕士。我居然考上了。住在校内的一位宿儒张尔田老先生(张东荪之兄),在燕京新闻上看见我的词,特把我叫去。听说我考上研究生,非要当我的导师,教 我学周邦彦词不可。这看起来也像是一条“辉煌”的路,将来再到美国哈佛大学走一趟,回来不难当一名教授。但是我想,我羡慕的是一二九、一二一六时期,走向 革命的那几个同学。他们离开燕京后,我常想起她们,并且对自己那时的糊涂、懦弱感到懊悔。现在又眼见更多的同学离开了,消失了,她们都在抗战前线接受炮火 的洗礼,她们都走向时代的前列。又有一些同学被捕了,可能已经为祖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我还念得下书么?或作什么“锦绣前程”的梦么?况且我未必不在危险 中。我和在昆明的妹妹、在陕西的朋友和即将由英国直赴内地的哥哥通着信,使我时刻担心敌人的检查。一次我在城内遭到一个喝醉了的日本浪人的追赶,倘不是两 个人力车夫设计跑散,救我逃过此劫,我恐怕遭大难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抗日。什么是自由?当时的燕园已没有自由。怎样去服务?我要到后方去教书,像我 的老师那样教书。
1939年寒假,我得到了和母亲一起经香港到重庆的机会,我要悄悄地离开燕园了。最后一日,我到朗润园郭师家辞 行,没料到他那么热情地支持我。我们对前途满怀信心地互道珍重而别。然后我回到宿舍,再出去把适楼、钟亭、琴室都巡视一遍,抚摸楼梯桌椅,穿过小径树丛, 最后来到未名湖,我深情地对它说:“抗战一定胜利,我必在胜利后回来!”进城后,我第一次找到了弓弦胡同顾宅,去向顾师告别。先生正在写一张条幅。上面一 首《临江仙》末二句是“一双金屈戍,十二玉阑干”,这是隐晦地以意境抒写囚徒之悲,我要了那张条幅,还要了两本书,一本词集,一本剧曲,都是先生的创作。 我详细地告诉他我的感受和心志,行程和打算,他连连说:“好!好!应该走,走吧!走吧!”随即用欢快的步子把我送出大门。我在重庆不敢给老师写信,一年多 后,我把送给他们的结婚请帖寄到燕大中文系,我想他们见到证 婚人张伯苓的名字,会猜到我是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的,那样他们就都放心了。
婚人张伯苓的名字,会猜到我是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的,那样他们就都放心了。
我在南开中学教英文和中文,正是我在燕京读书的实践和检验。七年半的教书方知当年在燕大读书生活之可贵。学与教正是人生的攀登之路,也是我这一辈子的黄金年 代。1945年抗战胜利,1947年复员返津,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才被调到北京,终于在以后的校友节中,我才重见久别的未名湖。
未名湖比从前更加光彩了,在充足的阳光下,它呈现着闪烁不定的灿烂的金波。我没有一丝伤感,只有重逢的高兴。因为它是变幻的,但又是永恒的,它是人生的缩 影,又是历史的见证。它和三十三年的燕京大学一起辉煌过,和那时的主人欢乐过、哭泣过;又和国立的北京大学达到更大的辉煌,和北大的主人一起改革、发展、 臻臻日上。
未名湖流在我的心底,因为我不能忘怀它,遗弃它,因为我一直在怀想它、感激它。那里有我的良师益友,我是在那里生长过 来的。它也不能忘掉那三十三年的燕京大学,那些非凡的学子,社会上出类拔萃的名医、名学者、名专家、名外交家,以及才人和教师,他们中几乎全是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三十三年中出现那么多人才?难道是渲染,是夸张?不,这是事实,历史是见证,未名湖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