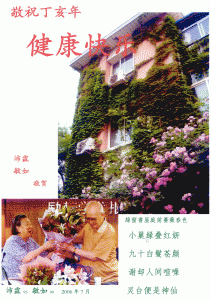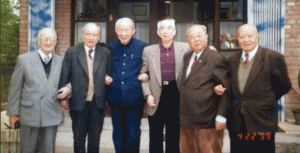2014-1-2 《中国航空报》沈英甲“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
季入隆冬,又到了年终岁尾。“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霄”。严寒的冬夜显得格外寂静,令人蓦然想起许多人和事。往年这个时候,我总会收到罗沛 霖院士用计算机亲手制作的贺年卡,上面签着罗老和夫人杨敏如教授的姓名,照例会称我为“英甲小友”。我仿佛还能听到杨敏如教授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为住在小 区里的老同志们讲解古典文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老同志们听得兴致盎然。如今,杨教授已经97岁高龄,志愿者的工作已经力不从 心,而罗老则已经故去一年多了,如果今天健在刚好百岁。
这一切正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永不止步的探索者
1999年10月,在我陪同王大珩、罗沛霖、崔俊芝、杨士中等院士来到巴丹吉林沙漠考察的时候,我以为自己见证了生命的奇迹。
王大珩院士当年85岁,罗沛霖院士当年86岁,当我跟随他们身后在五六层楼高的观测塔上爬上爬下不由气喘吁吁时,不禁问自己,如果能活到他们这个年纪,我还能做什么?
那年10月1日恰好是中秋节,在巴丹吉林沙漠安详、明亮的圆月下,罗沛霖院士得知我对使用计算机缺乏兴趣也一窍不通时,并没有流露出吃惊的表情,而 是慢慢说道:“你看,我现在的文稿都是自己在计算机上写的,连贺卡、寄信都是通过计算机完成的,方便得很。”大漠的寒风拂动着他们的华发,我本来想说诺贝 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就不会用计算机,但悄悄咽了回去。谁知回到北京后才几天,罗沛霖院士就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套“汉王笔”。
这真是难得的人生启迪!
从这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能够熟练灵活使用计算机了,成功“脱盲”。
有一件事我做得很后悔:在巴丹吉林沙漠考察的时候,他们提出想去敦煌看看,那里距敦煌大约有600公里的车程,这在大漠上是咫尺之遥。我反复掂量八 十五六高龄的份量,有关领导了解我的担心后也有点含糊了。为保万无一失,我把不去敦煌的意见告诉了他们,他们居然像商量好了一样,都报以微笑。至今他们都 没有去过敦煌。而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王大珩院士和我国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奠基人罗沛霖院士,分别以97岁、98岁高龄辞世。
当得知2002年王大珩院士又去了巴丹吉林沙漠,我后悔到了极点。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两弹一星”事业,王大珩院士就到过这片大漠。
写到这里,我不由再次地问自己:如果寿当耄耋,我能在巴丹吉林沙漠里站稳吗,我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做些什么呢?
一晃四年过去了,2003年10月,我约请罗沛霖院士为《科技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极具前瞻性,他预言在信息时代之后来临的应是一个文化信息时 代。毋庸置疑,当时年届九旬的罗沛霖院士始终在思考着科学问题,并在他的夫人杨敏如教授自豪地称之为“绿窗书屋”的寓所——一间布置得像机房的小办公室 里,用“汉王笔”写到深夜。他年事已高,视力衰退,字迹抖动,可见要写成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该多么不容易。
罗沛霖院士的不少论文都是在他进入耄耋之年后,一笔一画写成的。比如“跨入21世纪的先进文化信息技术系统”、“关于电子技术革命跨世纪时期的形 势”、“科学技术环节的选择”、“产业革命、文化产业革命和消费电子”等,每有发表都引起电子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他的论文“电子、文化主业的革命因 素”被著名的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录用为1994年远程信息系统学术会议论文,并安排他在综合组首先做报告。
2003年10月上旬,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坐在罗沛霖院士住所的客厅里,饶有兴趣地听他介绍9月的沈阳之行。2003年的中国科协年会在沈阳举 行,科学家们受到沈阳市人民的热烈欢迎,有124位院士受聘出任了沈阳市政府的科技顾问,接过聘书的124位院士中的最年长者便是年至耄耋的罗沛霖。沈阳 市的科技工作者对罗沛霖院士所做的“信息时代的来龙去脉和后因特时期”的报告至今津津乐道。在9月15日洋洋洒洒半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罗沛霖院士纵谈信息 时代,指出“文化信息在社会经济中作用明显”。他预言道:现代社会是信息时代,而信息时代的前途是文化信息时代。不管会出现什么新因素,例如生物工程、纳 米工程等,文化信息总会统领社会、经济的发展。
还让与会者们啧啧称奇的是,这位90岁的老科学家始终站立着做完了报告。
“君子喻于义”
像往年一样,如果罗沛霖院士健在,应当在精心制作圣诞节和新年寄赠亲友的贺卡了,虽然离年底还有半个多月。那年罗沛霖院士和杨敏如教授一起设计了贺 卡的图案:彩色打印的贺卡左下是20年前他们夫妇在厦门鼓浪屿的合影,右上是他们夫妇2003年的合影,笑容依旧精神依旧。画面中间是一扇绿影婆娑的窗 子,下书“绿窗书屋”。贺卡的上方是一行行草:英甲小友,恭贺新禧;下方横书:杨敏如罗沛霖敬贺。
我算是第一个得到这份珍贵贺卡的人。
我结识罗沛霖夫妇有些年了,已结为忘年之交,杨敏如教授常开玩笑似地说:“你喜欢我们家沛霖,别把他捧坏了。”
我和罗老夫妇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但已成忘年之交。我得空就去罗老家,赶上了就和两位老人一块儿喝下午茶——喝一杯红茶,吃几块精致的小点心,这是 当年他们在国外养成的习惯。我进门的时候,通常都是杨教授先和我打招呼,然后高声告诉坐在“绿窗书屋”忙着的罗老:“沛霖,沈英甲来了!”
接着罗老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缓步走出“绿窗书屋”,高兴地称我:“英甲同志!”罗老照例会坐在一旁,认真听我和杨教授的交谈。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罗老致力于回忆录的写作,兼以举荐和培养新人。我们曾约定,罗老回忆录完成后由我来整理。罗沛霖院士曾对我说,他要把手头 一些工作完成,然后潜心写作回忆录。我想,以罗沛霖院士皓首白头九十八岁高龄,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这部回忆录一定会是一幅内容异彩纷呈十分壮丽的人生画 卷。他的一生不知做了多少工程,但是这个工程他没有来得及“竣工”。
我和罗老夫妇的谈话内容可以说思接千载,凡人物、事件都入话题。我的忧虑、思考,乃至对科学发展的遐想,都愿意向他们倾诉。两位前辈都是世纪老人,丰富的人生阅历赋予他们深刻的洞察力。
父亲去世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都沉浸在哀伤之中,这种情绪很快被杨教授察觉,她很委婉地劝导我,要我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一天,从电视上看到一则 报道说,国外一些主流科学家搜集了人死后转世的不少实例,欲加以证明这是事实。我向来主张“科学没有禁区”,这次见面,我提出了一个话题:人死后有没有灵 魂?对此我思考过很久,也做过“研究”,那就是在北京许多家医院的太平间采访死亡,甚至去刑场观察。大自然创造出神圣的生命,最终又把它毁灭,那为什么要 创造出生命呢?我得承认,我既不能证有也不能证无。
杨教授向来会顾及我的感受:“父亲的去世你很悲伤,你希望存在灵魂,”她慢慢摇着头说:“人死去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转头看着罗老,希望他能说上几句。罗老只是面露微笑不置可否。
我和这些有幸同时代的科学巨匠的交往,最突出的印象便是他们从不摆架子,举荐新人从不存私念,不遗余力。
罗老很关心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注林左鸣同志在前沿科学方面的探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林左鸣同志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随时关注前沿 科学技术的进展,也在思考和研究许多涉及宇宙论、相对论、认识论,乃至物质、信息、生命本质等方面的科学问题,并撰写了一些颇有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论文。罗 沛霖院士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悉心批阅了论文,相信论文提出的假说能够经受时间的磨砺,历久而弥新,并满怀热情地向权威科学刊物推荐发表这些论文。显然,这 并不是每个科技权威都能欣然做到的。
在罗老病重期间,林左鸣同志专程去病房看望,罗老在病榻上努力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在他面前展开的科学杂志,虽然已经不能表达,但他的眼神露出了满意的光彩。
和罗老夫妇的忘年交几近完美,但是也存有不可弥补的遗憾。罗老写得一笔风格独特自成一家的书法,有朋友索字,他都不会爽约并很快写成奉送。知悉泥瓦 匠出身的农民工发明家赵正义破解了世界建筑技术百年难题的时候,他欣然命笔为赵正义题词:“十年潜心铸鼎,百代精英增君。”那么,给我题字该是应有之义 吧。罗老去世前不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故,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摔倒了,我闻讯赶去时,他脑门上已经缝了几针。对一位九十六七岁的老人来说,应是 闯过了一关。这成了一个转折点,罗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出于可以理解的考虑,我向罗老夫妇提出,请罗老写一副勉励的话,留作今后永久的纪念,他们爽快地答 应了,并告诉我,会仔细考虑写什么最好。然而来不及了,直到罗老去世字也没有写成。罗老离开后大概有一年多,我终于问杨教授:“罗老要给我写什么呢?”杨 教授告诉我,他们总想写一句最好最有意义,也最能概括我们友情的话。
这句话是“君子喻于义”。
如今这句话已经刻在我的心里,直到永恒。
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耄耋之年,罗沛霖院士还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就是和王大珩、张光斗、张维、侯祥麟、师昌绪几位老科学家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建立。
罗沛霖院士的人生画卷中有浓墨重彩的几笔,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是其中之一。
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著名电子学家罗沛霖就在考虑:中国要不要设置工程院。就中国科技界当时的认识而言,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基本技 术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技术科学的理解就谈不上那么清晰了。1978年,罗沛霖随团访美,这是一个中国电子学会代表团。在美国期间,代表团访 问了美国全国科研理事局,作为一个政府办事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三个国家科技院院士,也就是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院士,对重要科技问题进行研 究、咨询、讨论。当时美国科学院院士为1100人、工程院院士为700人、医学院院士为400人。其中医学院院士的人数是固定的,缺一补一。工程院院士的 目标是达到1500人。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罗沛霖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在《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杂志及《人民日报》等媒体上撰文,谈到了美国、 日本、西欧、苏联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强调了后进国家、地区赶上先进必须突出的重点环节。此后,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大会上,他又进一步明确指 出,科学技术中除基本科学和技术发展外,还有工程技术、生产准备、生产保持、推广应用、销售服务等更多重要环节。他强调,中国要重视基本科学,还必须更加 重视现场技术、基本技术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于是,罗沛霖院士再次提出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构想。为什么说是“再次”呢?因为在此之前,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张 光斗、张维等都提出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而且报到了中央,但是或许是时机尚不成熟,议案暂被搁置。此次罗沛霖再次提议成立中国工程院,理由充足多了: 不只是借鉴外国经验,更是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结合中国的实际,阐明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86年,罗沛霖创议并起草了 《关于加强对第一线工程技术界的重视的意见》,联合茅以升、钱三强、徐驰、侯祥麟等80余人,向全国政协提出了这一议案。仿佛成为惯例,罗沛霖及工程技术 界的一些同仁以精卫衔石填海的执著,在每届全国政协会上都要提出这个提案。
水到渠成的时候到了。1994年的春天,一天晚上,罗沛霖开始执笔草拟一份《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在此之前,罗沛霖已征求了 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几位老科学家的意见,由他们六人共同在建议上署名,呈给中央领导同志。在我1999年随王大珩、罗沛霖、崔俊芝、杨 士中几位院士去西北考察途中,还是在大漠上空一轮皎洁圆月之下,王大珩、罗沛霖两位老科学家不但谈到了他们的科学思考,也谈到了有关中国工程院成立之前的 一些往事。大家之所以公推罗沛霖执笔这个建议,一来他较早创议,二来坚持不渝,这份殊荣非他莫属。考虑到建议是向中央领导呈报,建议要写得言简意赅,一目 了然。为此罗沛霖颇费了一番心思。
罗沛霖终于下笔了,而且一气呵成。他在建议中写道:这个院的中心任务应是为国家、为政府的重大工程和技术科学决策以及技术经济问题,提供具有权威性 的咨询、论证和评议,对特别重大的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成果做鉴定。它理所应当地超脱部门和地区的局限性。为了完成这样的中心任务,其成员应是经过挑选的属 于国家水平的工程科技人才和对工程技术发展有重大贡献者,当然这也应是给当选人员在工程科技方面的最高荣誉。他建议,一位专家可以同时当选为两个院的学部 委员(院士)。这也就是罗沛霖、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等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来历,即所谓“两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初创阶段的院士也就是这样产生的。近几年,两院院士又增加了几位,与目前中国科学院750名院士、中国工程院807名院士相较,仍是凤毛麟角,足见荣 誉之崇高。
罗沛霖在建议中写道:在不久前的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增选中,许多产业部门很有成就的专家,以及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工程技术工作者,都未能纳入,也说明了建立工程与技术科学院是极端必要的。
在一次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一些科学家的时候,王大珩将建议呈给总书记。稍后,中国科协一份材料也刊登了六位科学家的建议。江泽民总书记非常重视,在 1994年5月11日做出了批示:此事已提过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国务委员宋健、罗干也做了批示, 拟请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牵头与有关方面商议办理。中国工程院呼之欲出。
1994年5月,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界迎来了一件盛事: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全国从事工程技术与技术科学的科技人员欢欣鼓舞,这是对他们神圣劳 动、奉献的庄严承认,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包括罗沛霖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成就了人生得意之笔。
1999年早春一个春雨淅沥的早上,经过一番费时费力且周密的张罗,我把王大珩、罗沛霖、张光斗、张维、侯祥麟、师昌绪六位老人约到一起,为的是拍 摄一张“全家福”,聚会地点是张维院士的家。张光斗就住在前楼,他年事最高可以逸待劳。我先到了张维院士的家门前,不一会儿,张光斗便穿着他那身四个兜的 蓝色干部服,背着手从后门踱了出来。冷不防,张光斗笑嘻嘻地一把抓住了我的左手:“你说,大学产业化行不行,行不行?”我觉得他把我的手抓得很紧,此时侯 祥麟院士已经到了,他的司机也笑嘻嘻地看着我。好在我思考过这个问题,连忙回答:“不行,不行!”张光斗这才松开了手。有传闻说,张光斗是这么一位老人、 老科学家,起先,清华大学有一个科学处,张老走到门前用拐杖用力敲打着科学处牌子:“技术还要不要,技术还要不要!”此后科学处便易名为科技处。
因为路远,最后到的是罗沛霖院士,他打了一辆夏利出租车赶来。这辆车被司机用得很惨,车门和车灯都用铁丝拴着,我用力把罗沛霖院士从半开不开的车门中搀了出来。
我的确得到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六位两院院士手挽手紧紧站在一起,他们的努力催生了中国工程院。后来这张照片被中国工程院拿去放大陈列在全国科技成就展上。现在,他们中的五位形神具融入了历史,健在的仅余师昌绪院士一人,这张照片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
“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这句话是俄罗斯伟大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已经在很多杰出探索者身上得到了验证。
如果从1928年罗沛霖参加南开中学无线电社开始屈指算来,他从事科学活动的时间已有70多年,这差不多是一个人的一生光阴了。
我国科技界多少年来都称罗沛霖是“红色科学家”,缘于他1938年初放弃了丰厚的待遇,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参与创建了八路军的通讯工业。也有人称他 是“三式(士)干部”——三八式、博士、院士。像他这样早年参加革命后来一直从事科技工作的科学家还有力一、侯祥麟、高士其等。有一些人中途改了行。
从倾向革命到投身革命,罗沛霖受到他的上海交通大学同学钱学森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钱学森早已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钱学森告诉罗沛 霖,读书救不了中国,只有政治活动才能解决政治问题,钱学森说的政治活动就是革命斗争。罗沛霖结识钱学森是在1933年,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70年。
在延安工作期间,他和战友们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向抗日前线输送了70多部电台,那时物质条件很差,完成这样的任务是很不容易的事。此后根据党的派遣,罗沛霖到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没有离开老本行电子工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战端再开,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党已经预见到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地下党的领导、后来的党的统战部长徐冰把一项艰巨的任务和一笔学费交给了罗沛霖:你设法去美国留学,开阔眼界,准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这是何等的远见!
对一个年已35岁的人来说,重入大学之门捧起书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罗沛霖说,他青少年求学时候,总是“懵懵懂懂”的,不过学习还是努力的。有人戏 言,罗沛霖凭兴趣读书,感兴趣的课程能拿满分,不感兴趣的课目成绩会差得异乎寻常。有了明确的学习目的和理想,罗沛霖回忆说,在美国加利弗尼亚理工学院学 习期间,“我每周学习、科学研究、工作70几个小时,有时天蒙蒙亮才睡。还克服了十二指肠溃疡的病痛。我的主课是电工,副课选取了物理和数学,有相当的难 度。那时我已35岁,离开学校生活也13年了,但我并不气馁,尽量利用我的理解能力,搞好各科学习。”
在22个月里,罗沛霖越过了硕士学位,直接获得了带特别荣誉衔的博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险象环生的地下工作中,杨教授给予罗沛霖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几十年来,她从未动摇过加入党组织的追求,在她年近九旬的时候,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伍绍祖同志的夫人曾晓前成为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罗老夫妇一生追求真理,最珍惜的是理想、信念、情操,还有气节。
1950年9月罗沛霖克服困难从美国回到祖国,为发展我国电子工业,为沟通学术界与产业界,奋斗了几十年,被誉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并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先后担任第一、二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谈到他的工作 时,他只举出参与组建了华北无线电器件联合厂(718厂)、参加制订《1957-1962年科学发展规划》、主持我国第一个超远程雷达和组织我国最早系列 (200系列)计算机研制中的技术攻关工作等几项。而他一再强调“只不过做了些开头的工作。这些工作最后都是别人完成的,仅此而已”。
2003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发射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安然返回,消息传来,罗沛霖欣喜异常,夜不能寐。我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回来, 兴奋地向他描述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情景,当时我处在离发射台比其他人都近的位置。夜阑人静,他在“绿窗书屋”兴奋得往来踱步,总觉着自己应当做 点什么才好。罗沛霖回想起1956年夏天,他和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等,就火箭及科技规划等各项紧急工作,向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黄敬部长、赵尔陆部 长、张劲夫等领导做了汇报。此后他的工作虽然与“两弹一星”无直接关系,但所从事的电子、信息科技却与两弹一星多有关联。他想到要给病榻上的老友钱学森共 贺盛举,“今‘神舟五号’圆满实现,国之大喜,因书俚诗,以奉学森作贺”,兴之所至,他熟练地打开桌上的计算机,操起“汉王笔”,于是一首七言律诗从笔下 奔涌而出:
千年古国梦飞天,十载攻关今喜圆。
筚路蓝缕君矻矻,功成业就自谦谦。
神龙腾起太空去,广漠迎来壮士还。
回念从前聂帅嘱,白头相庆共欣然。
钱学森教授的儿子、我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的老同学钱永刚在电话中说,他父亲已经收到了这首诗。想来这位老友的心情一定是“共欣然”吧。
“故人一别几时见,春草还从旧处生”。我没有告诉杨教授,罗老去世之后,我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罗老,在他的墓碑前伫立,与他 做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多么希望冥冥之中,他能再给我新的启示。在罗老的墓碑上,他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浓缩成“罗公沛霖神位”区区六个字。我暗想,这可能是出自旧学底子极其深厚,又恪守不居功不自傲,功成身退传统价值观的杨教授的主张,当然也可能源于罗老本人生前的交代。
“是真名士自风流”。希望将墓主人丰功伟绩传诸后世的墓志铭,省却了也罢!
罗沛霖院士留下的精神财富,会勉励我们终生。